
 36期
36期






女士们,先生们,你们应该都知道,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。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有一种被称为虫洞的现象,似乎最有希望帮我们实现物理上的时间旅行。时空中存在微小的扰动,使得时空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弯曲,然后从理论上讲,如果被扭曲的时空通过某种方式联通到了一起,不论这是偶然还是人为所致,在连续的时空中就有了一个虫洞。要是这个虫洞敞开的时间足够久,就能允许物体通过。这个物体可以是一个粒子,甚至可以是一个航天器,它从虫洞的这一端突然消失,然后突然在那一端出现。也就是出现在另一个时间或者空间。不过,想要做到这样的时空穿越,我们还需要控制这个虫洞的发生。如果你能创造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,并在同一时间创造相应的负能量物质,然后,如果你有某种手段把这两个黑洞连成一个通道,才能得到一个可供穿梭的虫洞。这么多“如果”堆积起来,希望真的十分渺茫了。从操作上讲,一点也不容易。
不过,幸运的是,我们还有其他的虫洞。它们十分古老,还可以让我们气定神闲地穿越时空。这就是人类的想象力。
在瑞典,我长大的地方,小时候大人教我说,不要随意叫醒看上去正在做梦的人。长大之后我发现这种观念实际上来自古老的维京传说。古代的维京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灵魂的东西,叫做“Hugr”。Hugr有时候会离开身体独自游荡,一瞬间就可以去到千里之外。比如人在做梦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。所以说,突然叫醒一个做梦的人是危险的:不巧的话Hugr来不及好好回到身体中,于是就会发生各种麻烦事。
所以我是想说,旅行,你不必真正亲身赶到哪里去。关于并不奔波的旅行作家,我最了解,而且最喜欢的一个例子,是法国贵族、军人泽维耶·德·梅斯特。他生于1763年,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,叫作《我房间里的旅行》。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踱步,日复一日,细致入微地描绘、讨论他看到的物件:铺了两张床垫的床,扶手椅,墙上刻的字,等等。他让自己的思绪游荡,思考生命和死亡和爱,思考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期望。他的小柜子上特别留了摆放书籍的空间,在那里他能找到:
“从阿尔戈英雄的远航到显贵会议;从最深的沟壑到银河系上最远的恒星;到宇宙的藩篱;到通往混沌的大门;四方上下,古往今来,我自由驰骋。我既不缺时间,也不缺空间。在那里,荷马、弥尔顿、维吉尔、莪相带我遨游。一切事都发生在那两个时代之间;一切国家,大千世界,万事万物都存在于那两个边界之间——一切都是我的,合法为我所有,一如每艘驶入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都合法地归某个希腊人所有。”
这就是另一种虫洞了,一定意义上说,和宇宙中巨大能量创造的虫洞一样强大。人类想象力的虫洞。
我是一个历史学家,不难从泽维耶·德·梅斯特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:囿于自己房间的限制,又超越边界,一次次在时间中旅行。或者至少,是在时间中寻路。历史既是一个学科,也是一种心态;在东方和西方,历史学几乎在同一时间诞生。(被誉为欧洲的“历史之父”的希腊学者希罗多德诞生的年份,仅仅是孔子去世的五年后。他们是同时代的人。)当然,历史学的同时诞生不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。它是文明进程的逻辑产物,究其内核,反映的是保存和传授先辈知识与经验的需求。虽然我们可以说,这台时间机器最早是用来向前走、通往未来的,但历史确实是一个通往两个方向的虫洞。它在相距甚远的世代与时代之间建立联系。
历史也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,在中国和西方无不如此。(因为历史就是文学写作。)在此基础上,还有一个中西文明之间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在于,虚构文学的产生要晚于历史写作。在中国,我们知道,小说和历史的类别区分是由公元8世纪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提出的。不过希罗多德和孔子都在各自的时代有过这样的区分,不过孔子的确要求更严格一些,他曾重点强调要记录事实,切忌他所谓的“道听而途说”。希罗多德不仅对道听途所毫无免疫,而且发扬光大:他还夸大了传言里的丰功伟绩。
这是历史学早期的一座里程碑:历史学者记录下他们看到或者听到的事,留下现世的图景以供后世之用。而相较之下,现代历史学在定义上是对于过去的关注,观察过去以供现世之用。(顺道一提,这种功利性也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雷区。)从实践上讲,现代历史学家处理的不是过去,而是过去的现代遗迹。
有时这正是挫折之源。你感觉被困住了,就像泽维耶·德·梅斯特一样——梅斯特实际上就是被困住了,他因为得罪了当局,被软禁在意大利都灵的家中。你感觉被关了禁闭,因为你只能待在你的房间里,你的桌前,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事,从来没有亲口与你笔下的人物对话。那些人早已作古,我所知甚详;我曾经幻想过,自己可以付出很大代价,不至于牺牲我的右手,但可以是右手小拇指,以换取与他们对话30分钟的机会。这一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。做一个历史学家,你注定总是迟了一两个世纪才到达现场。
冲出禁闭的渴望,去亲自见证的渴望,促使我去世界各地游历,偶尔做一下战地记者。90年代我去过巴尔干和阿富汗,2005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也在伊拉克。我还能有什么怨言呢?是的我确实亲眼看到了,但是我到了比如喀布尔或者巴格达,我发现了一个很多人早已经历过的困境:置身于历史事件当中,并不能保证你能够理解它们。你被困在混乱、嘈杂的现实当中,有可能地球另一端的编辑部都比你更明白发生了什么——所以历史学家就是这么矛盾,他们常常比当事人更理解发生的事。你会明白,距离常常是构成理解的要素。但距离的代价,就是你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亲身经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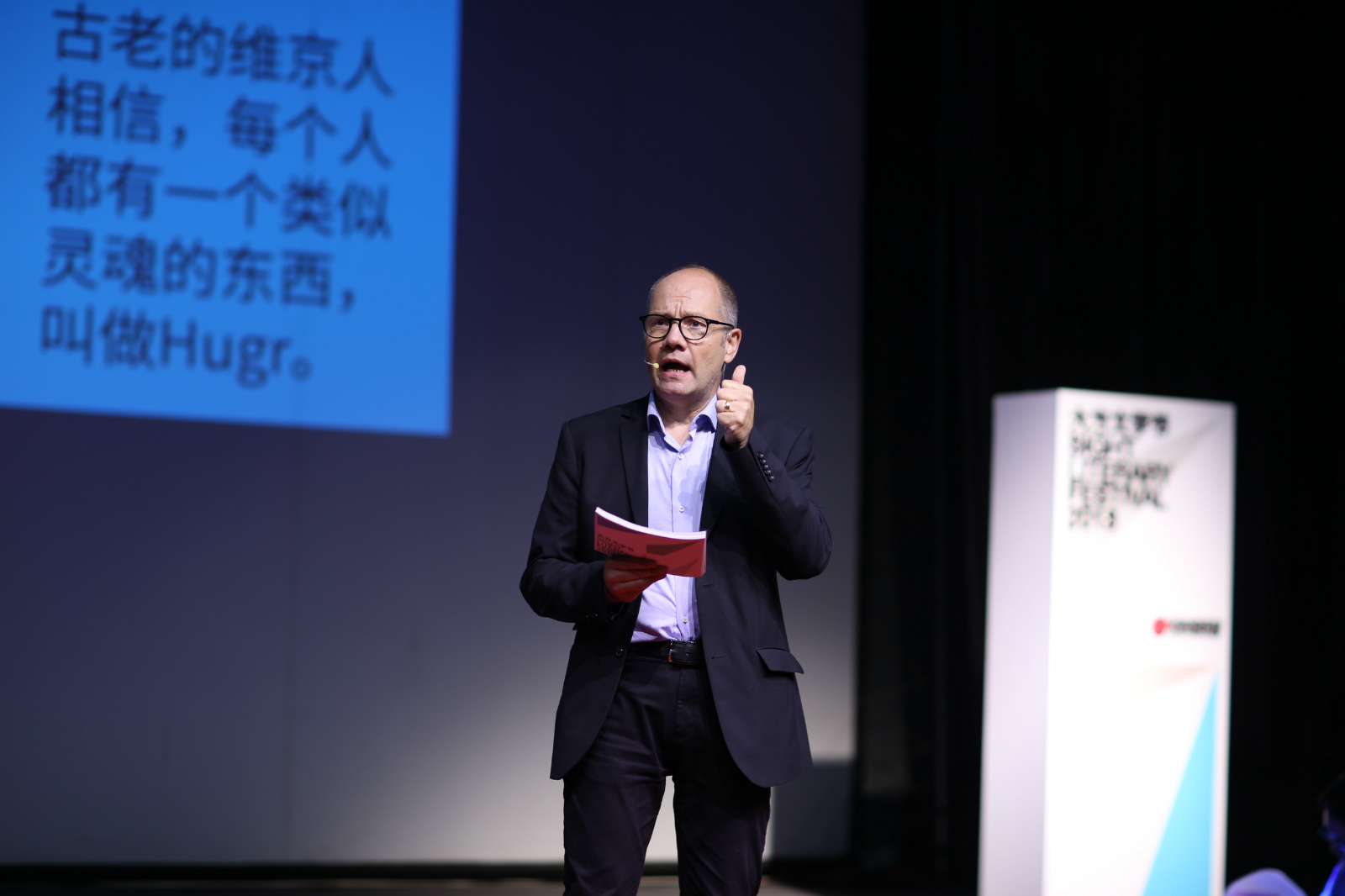
所有的历史学者都知道,这两者是难以权衡的。我觉得,在历史学的帮助下回到过去这一意愿,预设了我们能接触到生活在那时那地的普通人,他们的日常细节和思考。这当然并不总是容易实现的。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消失得毫无痕迹。没有办法把他们重新挖掘出来。历史学的时光机器只能运转在事实之上。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,那虫洞只能是一个黑洞,让你无法从中再出来。
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。正如我刚刚提到的,中国的孔子和希腊的希罗多德都已经明确了这一区分。让真与假的混沌不清,让情感取代了理性的位置,让共同经历的真实被忽视,你将陷入麻烦。很深,很深,很深的麻烦。20世纪所有那些人为的灾难,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,都因幻想而起——无他,都是想用虚幻的理想之乡模仿现实,让现实在一段时间里遭到漠视。但是真实终将取胜。真实的分量从来不说谎。
在写作方面,现实与虚构的区别也很重要。作为一个历史学者,我对于现实与虚构混合的写作,总是难以接受。历史学者就是不能这么做。永远不能。如果你是一个虚构文学作者,你当然可以混合真实与编造,但是也不能对自己说谎:你最后写出来的东西,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虚构文学,不论你在你的混合物中加入了多少完全真实的元素。历史与虚构文学分属不同领域。它们是存在于不同本体论层面的两种现象。做到尽善尽美的历史就是一台时光机,可以实现时光旅行,带你去看一个另外的时空。啊哈,我听见你们私下嘀咕了:历史小说又是什么?在我看来,历史小说是关于当下的寓言,正如科幻小说也是一个探索当下世界的巧妙手段。忽略表象,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是一种只能把你带回当下的时光机。它们的目的也正是如此。
小说作家的那种自由想象,心智允许他做的,他都应该乃至必须做。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想象,并不是这种小说家的想象,而是历史学者的想象:收到事实的约束,在事实之上生长,除了寻找真相之外没有别的目标。有人说,旅行者有两种,一种是靠地图旅行的人,另一种是靠罗盘旅行的人。两种工具对文学漫游者来说当然都有用,但是如果比如二者择一,我会选择罗盘。罗盘从不说谎。地图只不过是大地的画像,不能把它错当作大地本身。这里,不妨回想一下杰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的一篇非常短的短篇小说(顺带一说,他本应该得到诺贝尔奖的),他写到一个帝国,其中:
“地图绘制的技艺已经至臻完美,一个省的地图铺开就会盖住整个城市,全帝国的地图铺开就会盖住一个省。不久,人们不再满足于这些不忠实的地图,制图公会制造了一张和帝国国土一样大的全国地图,把国土上的物体一比一忠实复制。帝国的后代人不想前人那样热衷地图学,他们觉得这么大的地图毫无用处。他们把地图铺到了烈日与严寒肆虐的不毛之地,此举实在难脱暴殄天物之嫌。在帝国以西的沙漠里,至今来残存着这幅地图的碎片,上面居住着流浪的动物和人;除此之外,世界上就再没有别的地理学问的遗迹了。”
没错,地图是有用的。但是它们代替不了真实的土地。有时你必须从那间禁室中走出,行走在真实的世界中,因为旅行意味着将某些事物置于险境,将你个人的幻想置于险境——你关于某个地方、某种理念或者关于自己的幻想。旅行总是某种追寻。
人类的很多最古老、最基础的叙事常常有旅行的情节,这看来也是情理使然的事。人,身为个体生活在种种限制之中,单薄地存在于此时此地。旅行在终极意义上,是对个体限制的超越,参与到无数的他人的生活里。这不在乎我们的旅行是游走在脚下这个世界,还是独自待在房间里,让自由、开放的头脑穿过想象力的虫洞,乘着我们称之为“历史”的时光机。


 79期
79期

沪ICP备06026464号-4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
沪网文[2014]0587-137号
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许可证:0911603
©2011-2019 qingting.fm ALL Rights Reserved.
应用名称:蜻蜓FM | 开发者:上海麦克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